- 話題
106k 帖子
65k 帖子
62k 帖子
57k 帖子
54k 帖子
47k 帖子
44k 帖子
44k 帖子
42k 帖子
- 10#NADA#
40k 帖子
- 置頂
- Gate.io 全員交流群“芝”心好友,感恩有你”感恩節活動開啟!
感恩節精美周邊大放送,加入Gate.io 全員交流群,暢聊社區,發言贏精美周邊,還有合約體驗券、感恩節幸運大獎、海量紅包等你來拿!
🎁福利1:發言前十
第1名:金牛雕塑 + 十週年紀念章
第2名:潮流藝術滑板 + 平沿帽
第3名:電腦雙肩包 + 帆布袋
第4名:多功能充電器 + 隨行咖啡杯
第5名:品牌雨傘 + 品牌冰箱貼
第6 - 10名:平沿帽 + 帆布袋
🎁福利2:幸運參與獎
隨機抽選發言條數不低於200條的20名用戶,每人獎勵$10合約體驗券
🎁福利3:海量紅包雨
Gate.io全員交流群將在感恩節11月28日
- 📢 #Gate观点任务# 第五十四期精彩啟程!調研Peaq network (PEAQ)項目,在Gate.io動態發佈您的看法觀點,瓜分$100 PEAQ獎勵池!
💰️ 選取10名幸運參與用戶,每人輕鬆贏取 $10 等值 $PEAQ 獎勵!
👉 參與方式:
1.調研Peaq network (PEAQ)項目,並發表你對項目的見解。
2.帶上Peaq network (PEAQ)現貨交易鏈接:https://www.gate.io/trade/PEAQ_USDT
3.帶上Peaq network (PEAQ)永續合約交易鏈接:https://www.gate.io/futures/USDT
- 🎉Gate.io動態熱聊板塊積分任務正式上線!
💡完成熱聊任務,輕鬆贏取榮譽積分!
❓如何參與:
1. 打開Gate.io APP幣圈-動態,點擊頭像旁的積分中心
2. 點擊下方熱聊即可看到積分任務,點擊“去完成”完成任務即可獲取榮譽積分
3. 立即加入熱聊:https://gateio.onelink.me/LHro/group?chatroom=group
✅ 每日首次發言 +60積分
✅ 每日完成10次發言 +60積分
✅ 每日分享交易卡片(最多3次) +30積分
參與熱聊積分任務,一邊分享投資心得,一邊賺取榮譽積分,解鎖更多福利!🎁
- 🚀 Gate.io【精選】標識功能正式上線!發佈你的加密洞察貼,瓜分$100獎勵!🎉
在Gate動態發佈你的原創內容,將有機會獲得“精選”標識。被選中帶有精選標識的內容不僅能獲得更多榮譽積分和流量曝光,還有機會瓜分$100獎勵!
🎯 如何參與:
1.填寫表單報名:https://www.gate.io/questionnaire/5531
2.發佈你的原創帖文
3.官方會根據您發佈的帖子內容和質量給予“精選”標識
📅 活動時間: 2024年11月25日 24:00截止
🎁 獎勵詳情:活動結束時,官方將從所有獲得精選標識的報名用戶中,隨機選取5-10名優秀創作者,瓜分$100獎池!
�
- 🎉 We Want You 👉️成為Gate.io 動態幣圈觀察員,超值獎勵天天領!
📈 你我都是“幣圈觀察員”,掌握前沿消息,解鎖財富密碼!
🌟 如何參與?
1、在動態分享幣圈每日前沿新聞、行情熱點、Crypto觀點、行情分析等內容;
2、帶上 #币圈观察员# 標籤,即視為成功參與。
將在每個工作日隨機選出5位優秀的“幣圈觀察員”,每人獎勵$2代幣!
📌 獎勵名單將每日選取公佈,獎勵發放將於次周統一發放。
📌注意:帖子不得包含除 #币圈观察员# 之外的其他標籤,否則將無法獲得獎勵。
「各位幣圈觀察員們還可以報名參與成為 Gate.io 動態大使,贏取專屬獎勵、獲得Gate.io精
央行副行長陸磊:貨幣與貨幣循環、貨幣政策與中央銀行、數字時代的世界貨幣
來源:數字法幣研究社
導讀
本文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陸磊在《貨幣論》撰寫的自序。
寫《貨幣論》的動力來自一次回鄉之旅。作為一個具有研究本能的經濟學教師,我不願意放過任何基於現實情況的理論思考。2020 年8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帶著妻女坐在京滬高鐵“復興號”列車上,孩子一邊聽著心儀的歌曲,一邊做二次函數習題,我把臨行前隨意帶在包裡,一半用於重溫、一半用於催眠的 Friedman 和 Woodford(2011)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3A 卷打開,很快被 Williamson 和 Wright(2011)所著的《新貨幣主義經濟學》(New Monetarist Economics)一章所吸引。吸引我的原因是,兩位作者均兼具中央銀行工作人員和大學教員的雙重身份,與我近似的履歷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鳴。但是,目光在書頁上,我的思路卻隨著呼嘯的列車在飛旋——美國史無前例地實施無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已經數月,為什麼股票市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期間經歷了 3 月的數次熔斷,之後又創歷史新高,但是此間的實體經濟尚無明顯改善跡象?4 月的 CME 原油期貨價格竟然呈現負值,但黃金和數字貨幣價格持續攀升,那麼,世界貨幣體系是否會發生變化?顯然,這是一些貌似簡單的現實問題,似乎 15 分鐘的思考甚至嘲笑市場的非理性就足以使我轉向更有價值的閱讀。但是,就是這些簡單問題,伴隨著我度過足足 5 個小時的車程。這是因為,這些貌似簡單的問題並不能從厚厚的手冊中找到完全能說服我的答案。
夕陽中,當我們三人在江南某個小站的站臺上,拖著長長的影子向出站口走去的時候,我看著身邊呼嘯加速駛向上海的列車,對妻子說了一句話——“可能,我教過的貨幣經濟學存在部分基礎性 bug(瑕疵),我觀察到的事實、所做的工作與所講的課程完全是兩個樣子”。
一向願意鼓勵我且同樣長期從事過金融學教學工作的妻子充滿期待地對我說:“那你就照你認為的樣子重寫貨幣經濟學好了。”
“好吧,但是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對。”我鄭重其事地點點頭。
“那也不一定錯啊,試試總沒錯!”女兒聽到我們的對話,俏皮地插話。
值得一試。但是,當時我完全沒有認真考慮這件事情的可行性。系統性的工作需要系統性的時間支持,看來,我只能利用零碎的時間實現思維的拼湊。好在我可以跟我的學生——劉學博士進行碎片式的觀點交流,再從彼此的砥礪中凝練不同(雖然不一定完備)的視角,提煉真正有價值(雖然不一定正確)的觀點。
至少在經濟學領域——我不知道其他學科如何——在系統訓練的基礎上,直覺是十分重要的東西。有一部藝術性很強的電影——《美麗心靈》,以數學家約翰·納什(John Nash)為原型,從我的非藝術性角度去理解,就是說明了直覺的重要性。在我 30 年的職業生涯中,15 個年頭在高等學校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貨幣金融學》(使用過黃達、周升業和曾康霖、Mishkin 以及陳學彬版本)、《微觀經濟學》(使用平新喬、Varian 以及面向博士生的 Mas-Colell、Whinston 和 Green 版本)、《宏觀經濟學》(使用 Mankiw、Romer 以及選講章節的 Ljungqvist 和 Sargent 版本)、《數理經濟學》(使用 Takayama 版本)、《貨幣經濟學》(使用 Walsh 版本)等理論課程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使用我依據在商業銀行的工作經驗自編的講義,參考曾康霖版本)、《信用風險管理》(使用 Colquitt 版本)等實操性課程,另外 15 個年頭在中央銀行、外匯管理部門、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機構從事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一個揮之不去的直觀感受是:貨幣經濟學教學與貨幣金融政策實踐之間始終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當然,我在教書的時候,就按教科書給學生講;在從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研究以及提供政策執行建議的時候,就按政策規則經驗提出操作建議。但是,在 2020 年 8 月的那個傍晚,我下決心用可能 10 年的時間來致力於彌合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
下這個決心需要勇氣。一方面,凡涉及框架性重構的理論研究所製造的對立面不是一兩個人,而是幾代甚至十幾代人——比如我在北京、深圳、成都、廣州漂泊間幾乎須臾不離的《貨幣經濟學手冊》中的所有令人尊敬的學者。這會讓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備尋找貨幣世界真理的現實條件。另一方面,科學思維中最投機取巧的做法是“舉一反例”以推翻既有定理,但是創建某種新的認識框架要艱難得多。這就是我對 Wray(2012)所著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Theory,MMT)抱有高度敬意的原因。恰如 Keynes(1936)所說:“經濟學家或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正誤,都比人們通常相信的更加有力”,因此,我堅持的貨幣經濟學批評(critique)實際上應該是一種框架的創建,而非一句話否定一個框架。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假如理論與現實之間真的存在鴻溝,那麼,是理論錯了,還是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有誤?這就涉及認識論層次的討論。一方面,無論對錯,我一直堅信理論只能是對現實的主觀理解。或者說,現實不存在對錯問題,僅是客觀事實。因此,理論若無法反映事實,那麼有待修正的只能是理論。另一方面,無論對錯,我同樣一直堅信理論的解釋力是具有時間和空間侷限性的。比如,關於鑄幣稅的研究僅僅是因為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生產與其他國民經濟部類的生產函數幾乎完全不同,因此在產權意義上,任何貨幣增發都意味著政府憑空增加了購買力,也就攤薄了流通中貨幣的購買力,故形成事實上的“徵稅”。然而,在當前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貨幣發行體系下,貨幣發行實際是對金融機構和借款人的補貼,只要政府不是債務人,就不會在此進程中獲取任何稅收。之所以用這個例子,是因為作為一個教員,我發現從貨幣、貨幣需求、貨幣供給、貨幣政策到世界貨幣,相當多的理論論斷實際上還停留在我們人類曾經經歷的金屬貨幣時期——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 或 Mundellian Trilemma)理論等。
我們所處的貨幣經濟是成長中的,任何刻舟求劍式的固化思維都會在快速變化的現實面前碰壁。這就好比我的女兒,而今正當豆蔻年華的她,與 10 年前情緒化且言聽計從的小姑娘相比,有著不可逆轉的成長性、顛覆性變化——雖然依舊溫婉而奔放,但自從讀書以來,增加了理性而富於獨立思考的特質。我的感嘆是,我無法再用當年的方式來理解她並與她相處。同樣地,也許我們無法再用同樣的模型來完全理解並參與或影響此時的貨幣經濟。
儘管,在名字上,她依舊還是那個她;在定義上,貨幣也依舊還是那個貨幣。
曾經的理論在曾經的歷史時空中並沒有錯,我們需要的是理論隨著時事變遷而不斷迭代的思維方式。
《貨幣論:貨幣政策與中央銀行(第二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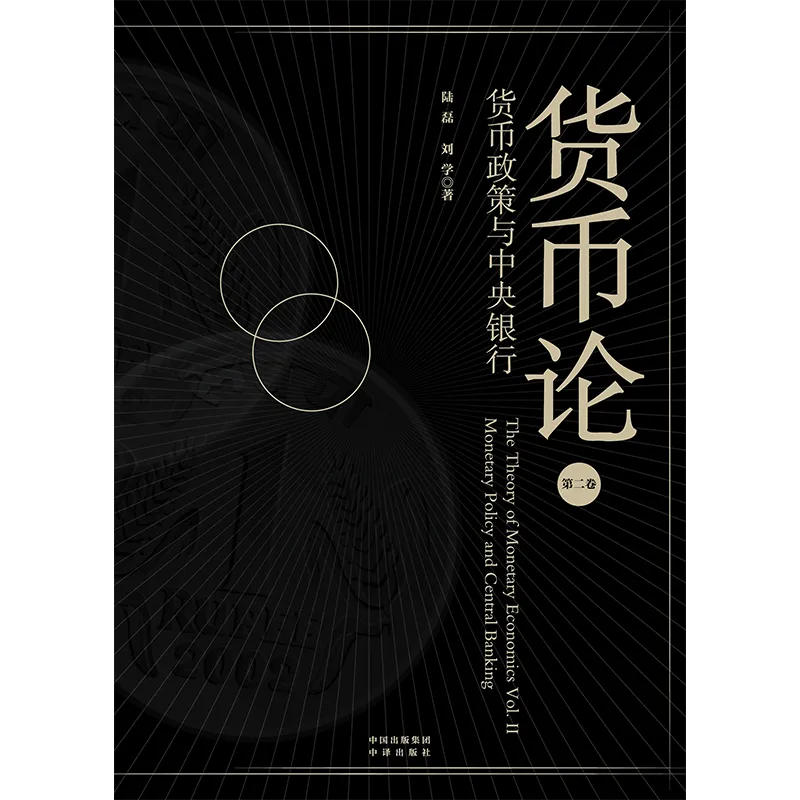
一般而言,思維過程是由表及裡的;思想呈現是由內而外的。
我想,這是所有理論研究的通常方法。具體講,我們往往因一些具體事件引發研究衝動,但是在寫論文時,卻往往先描述一般理論,再以引發研究的具體事件作為實證依據。我與我的合作者劉學博士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多數場合,我們總是圍繞有趣的事實而非枯燥的數理研究進行討論甚至爭論,當然,作為教師,我難免以高壓態勢結束爭論。但是在《貨幣論》的三卷呈現中,讀者們看到的必然是模型推導和一系列定理體系。在此,我們深表歉意。數學也許不一定是表達觀點的最佳形式,但至少在目前,語言文字仍然存在較大的自由解釋甚至各取所需的空間,數學是避免歧義並保持邏輯上的動態一致性的最佳手段。
問題的提出都是由表及裡的,比如表面現象是那個著名的蘋果,而內在實質是萬有引力。根據我的研究初衷,2020 年 8 月的那個蘋果給我的直覺衝擊僅僅是“貨幣存在大量發行的空間,事實上,各國正在這麼做。而且,貨幣放水造成牛市,各方都很開心”,這對我而言,卻是一件沮喪的事情:在疫情的衝擊下,貿易、投資、消費全面萎縮,全球的唯一亮點竟然是發行貨幣且資產價格猛漲!無論如何,上述現象級衝擊都在顛覆我篤信多年的貨幣經濟學原理。但是,通過在理性層面研究上述現象,很快我就發現存在三個極其具體的理論問題:第一,我們如果要確定貨幣會造成資產市場牛市,那麼首先需要明確貨幣是如何進入資產市場的,或者說,憑什麼斷定貨幣缺乏進入實體經濟的積極性。第二,如果貨幣增量能帶動且僅能帶動資產價格上漲,那麼其一定與產出和通貨膨脹均無關。這樣的貨幣效應應該如何界定?現有的貨幣政策規則是否失靈,應該怎樣校正?第三,如果中央銀行可以無底線,貨幣發行可以無上限,那麼貨幣很可能被其他一般等價物所取代——比如當前市值震盪上行的數字資產和穩定幣。真的會這樣嗎?作為長期在中央銀行從事研究工作的我,直覺上浮現的想法是,主要發達經濟體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從中央銀行家手中挽救中央銀行”。儘管這一思路絕非當前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因為我認為 CBDC 毫無改變貨幣增量的制度含義,但是,是否存在一種既能克服各類數字資產的衝擊,又能實現穩定幣效應,還能保持主權貨幣存在性(解決歐元的貨幣統一但財政分散問題)的數字貨幣?
所以,我們的三卷本《貨幣論》針對的表面現象以及由此探究的基礎性現實問題實際上正是上述三個現象級衝擊。這也是我們分三卷實施平行研究的原因。三卷分別解決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卷《貨幣與貨幣循環》試圖解釋貨幣如何流通;第二卷《貨幣政策與中央銀行》試圖解釋貨幣政策如何發揮效應以及貨幣政策規則應該被如何修訂;第三卷《數字時代的世界貨幣》試圖為主權貨幣如何應對非主權數字資產和超主權貨幣的競爭出點主意。
《貨幣論:貨幣與貨幣循環(第一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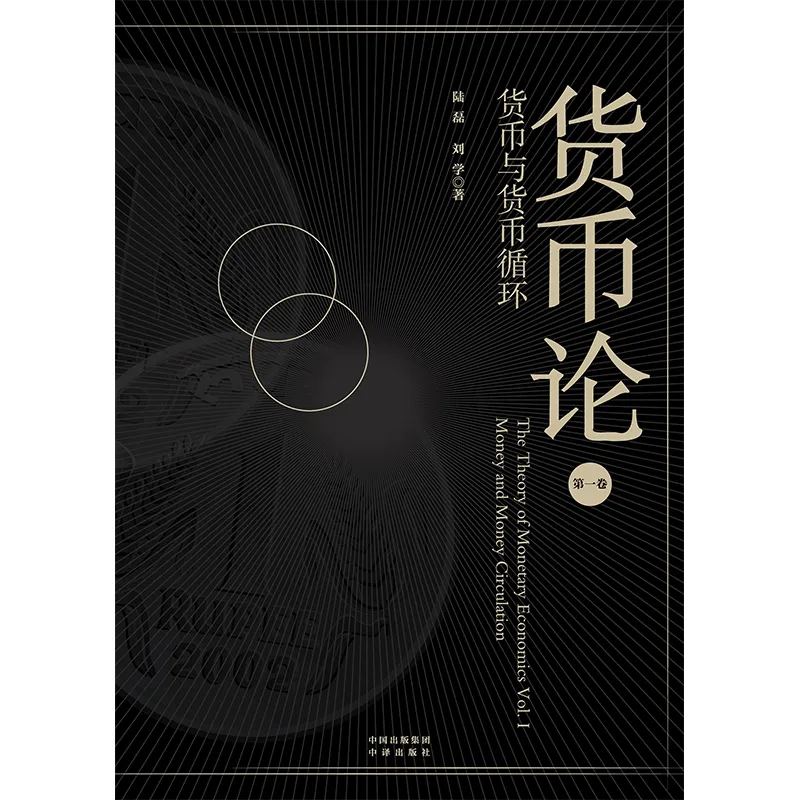
第一個問題:貨幣究竟流向何方?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決定了我們如何真正理解貨幣與貨幣循環。我們的討論發現,這是貨幣理論與真實世界脫節最為嚴重的地方。
第一個表象是脫實向虛的疊加態。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過於冒失地把立足金融市場的服務性行業定義為“虛”,把第一產業、製造業和其他服務行業定義為“實”。實際上,任何一個企業或個人,都可能是虛實疊加的。比如,某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很可能同時存在自有生產性資本形成和對其他非生產性相關資產的投資及其收益。比如,即使某人購置房產是自住的,但他的確因此獲得了房地產市值漲跌所造成的浮盈或浮虧。比如,金融服務業的增加值可能既來自服務和資產負債撮合,也來自套利性自營。因此,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虛實二分法,而在於一個經濟體的貨幣循環是否存在套利性激勵。
第二個表象是貨幣增量的疊加態。關於貨幣增長是否僅僅造成通貨膨脹,抑或在造成通脹的同時帶動了經濟增長,即貨幣增長的名義效應和實際效應究竟如何,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處於站隊式爭論狀態。這是古典學派和實際政策操作中持續面臨的問題——儘管各方都相信貨幣增量不一定帶來產出增長,但在真實世界裡,經濟下行一般都伴隨著外生貨幣擴張。因此,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貨幣中性與非中性二分法,而在於貨幣當局測量貨幣效應的時間長度以及把貨幣增量帶來的影響實施貼現的時間長度——短期的非中性和長期的中性疊加。
第三個表象是金融中介在貨幣供求中的作為。幾乎所有的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教科書都僅僅把金融中介作為溝通儲蓄與投資的橋樑,前沿性研究則立足於微觀經濟學,圍繞金融中介的信息對稱性、跨期定價、借款人與金融機構的博弈做極其複雜的數理研究。這些研究所隱含的假定是:金融中介在宏觀上是無關緊要的——它僅僅是一個橋樑和篩選機制。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若數字時代的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則“儲蓄—投資”可以被大數據(我們可以想象為一臺具備超級運算能力的計算機主機)自動撮合,由此可以解釋互聯網金融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問題是,這種判斷存在假設上的根本性缺陷——金融中介不僅僅背靠公眾,還背靠中央銀行,其具備的資產池能夠輕易實現跨期和跨資產類別補貼。因此,金融中介不是社會經濟主體信用的加權平均(如果是,則金融中介無關緊要,其僅僅從事撮合這樣的技術活),而是具有獨立的、高於社會經濟主體信用水平的行業。由此得到的石破天驚的結論是:金融中介是貨幣需求者,而公眾是常規貨幣供給者,中央銀行是備用貨幣供給者。
第四個表象是貨幣交易。自李嘉圖、馬爾薩斯以降,太多的學者在貨幣與商品之間的交易中尋找靈感。既然貨幣是特殊的商品,那麼它應該可以被寫進效用函數,比如 Sidrauski(1967)的模型。這種混沌認知直到天才般的 Debreu 和 Arrow 發現貨幣在一個具備完美期貨交易市場的經濟中本不必存在才被打破(參見《貨幣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第一章)。在我和我的博士生們(主要來自中央銀行、銀行監管部門和金融中介機構)討論的過程中,我做了一個大膽推斷——如果我們沒必要那麼複雜地思考問題,僅僅把貨幣作為一個制度性現實存在,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限定一下真正有意義的貨幣交易?在他們的一臉惶惑中,我說,如果我們試試把貨幣交易定義為貨幣與貨幣之間的交易,一切會變成什麼樣?聰明的他們馬上理解了——貨幣交易是同一貨幣的跨期交易,也是不同貨幣的即期交易,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貨幣理論勢必變得符合真實世界。
第二個問題:貨幣政策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於我和劉學博士對 20 世紀 90 年代的日本和 2008 年後的美國及歐洲中央銀行的政策檢討。所討論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1990 年,當時號稱“平成鬼才”的三重野康實施再貼現率上調的政策對不對;2008 年,伯南克與保爾森不救助雷曼兄弟但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決策是否最優;2020年,美聯儲的平均通脹目標和無限額量化寬鬆政策對經濟的實際效果是否得以顯現等。我們的討論可以說充滿了火藥味——作為教師的我一度很難說服作為合作者的學生。這是因為,一旦進入具有顛覆性討論的領域,與其說是教師與學生的爭論,不如說是我們雙方固有的貨幣經濟學“常識”與一系列不符合常識的“現象”之間的衝突。很多次,我只能以教師的威嚴壓服我的學生。令人長吁一口氣的成效是,我們在諸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第一個共識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我們的“常識”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天然地處於“自上而下”的狀態。因此,當我們認為政策正確時,如果最終效果與政策初衷存在偏離,我們往往會得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結論。對此,我對學生的詰難是:中央銀行到底是貨幣經濟的深度且直接的參與者,還是監督者和校正者?顯然,中央銀行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後者。那麼,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定具有“自下而上”性質,即貨幣交易和貨幣創造的主要功能依託於金融中介的信用創造,中央銀行當且僅當發現貨幣交易存在梗阻(比如錢荒或資產荒)時才會出手。所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多數情況下的自下而上和少數情況下的自上而下的組合。
第二個共識是貨幣政策的超級中性。各國都在關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貨幣增長和負債率。如果貨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發行,那麼既然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是外生決定的,是否在邏輯上可以認為中央銀行是資產泡沫化的始作俑者?原本我們的爭論在於貨幣政策的中性與非中性二分法,在我一再強調“任何模型推演必須符合真實世界的貨幣運行”時,我們取得的共識是: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疊加態之外,還存在另一種貨幣政策形態——貨幣增量的超級中性,即如果實體經濟已經實現了貨幣配置最優化,那麼任何貨幣政策所導致的貨幣增量變化,既不造成產出變動(即沒有實際效應),也不造成物價變動(即沒有名義效應),而只形成資產價格變動(因為缺乏更好的定義,我們只好給出“超級中性”概念)。
第三個共識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存在上下限。2008 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先後實施量化寬鬆和非常規貨幣政策,此後的2020 年,各國中央銀行再度實施擴表,我們的爭論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是否存在永續擴張的可能性?在暗中嘲笑中央銀行的中本聰先生似乎正是抓住了擴表的軟肋——總有一天,貨幣無度發行會使中央銀行走向末日,不能否認的是,這是簡單而符合供求規律的認知。我的擔心在於,會不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方面,貨幣助推資產泡沫化,反噬貨幣自身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特定資產(比如數字資產)的日益昂貴,使得其也走向自己的反面,缺乏作為一般等價物所必須具備的流動性(即被收藏,而非流通,這是貴金屬退出貨幣的宿命)。那麼,迴歸到本源問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真的可以無限擴張嗎?我們的答案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存在上下限。下限是潛在經濟增長與實際增長的缺口所要求的資本存量變動額,即居民存款貨幣與資本形成所要求的信貸增量之間的差。上限是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規則決定的額度,應該等於金融中介體系壞賬與銀行資本金的差。
第四個共識是宏觀審慎管理無法獨立於貨幣政策。自 Borio(2003)系統性提出宏觀審慎管理的基本思路以來,在貨幣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之外增加了一個金融穩定的重要支柱,其基本含義是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者應該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源配置的順週期行為實施特別管理。由於我在過去七八年間幾乎痴迷於宏觀審慎管理研究,在過去 20年間因為對日本和韓國大型銀行業發展及其危機的關注而特別相信“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規制勢在必行,因此,我至少有兩個博士生已經以此作為論文專題。但是,在與劉學博士的討論中,針對 2008 年至 2020 年的中央銀行實踐,我們很快達成了共識:進入 21 世紀,貨幣當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機構的“大而不能倒”,而是更深層次的金融資產的“漲而不能跌”(too high to fall)。原來的金融穩定理念基於金融同業之間的交互資產負債連接,因此大型機構的流動性問題往往對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具有致命影響。但是,隨著所有金融機構持有資產的“單一化”與“同質化”——比如債券、房地產抵質押品,資產價格波動對所有金融機構的影響是一致的。那麼,利率和匯率等基礎性價格——或者,最根本的是利率,如果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匯率的話,那麼其對系統性風險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一切宏觀審慎管理最終都無法離開貨幣政策而獨立存在。在宏觀審慎管理工具上,多年來處於探索階段的“貸款價值比”(Loan to Value,LTV)與微觀審慎監管的資本充足率一樣,很可能陷入軟約束悖論:如果資產價格被貨幣不斷推高,貸款當然可以更高;如果人為限定資產價格,那又將導致定價缺乏憑據的窘境。與此類似,金融機構在資產膨脹階段,大概率會補充資本金而不會削減資產。因此,兩種貌似是硬約束,實際上卻可能淪為泡沫和信用風險的助推劑。事實上,各國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上述現象並非主觀臆測,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和劉學博士在面面相覷中苦笑——人類的金融穩定理論可能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那麼,返璞歸真的簡單思考或許只能是,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發行或回籠貨幣)仍然只能是保障金融穩定的唯一現實良方。
第五個共識是財政與貨幣當局互為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自 MMT 誕生以來,財政與貨幣的關係這一古老命題再度成為熱議焦點。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中,我和劉學博士發現:儘管拋棄頭腦中的固有觀念很難,但我們不得不首先做一項工作——完全的實證而非從規範出發。那麼,問題就演變為——中央銀行和財政當局在現實世界中的關係到底如何?我們形成的共識是,雙方互為 SPV。一方面,財政政策把中央銀行作為 SPV,儘管國債和市政債的原始購買者是金融中介,但中央銀行出於流動性管理要求會通過回購吞吐作為高等級債券的政府債,因此,穿透看,財政收支的重要夥伴或 SPV 是中央銀行。在爭論中,我們同樣形成共識的是: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貨幣發行已經不再具備鑄幣稅的內容。這是因為,貨幣發行的生產函數與傳統金屬貨幣時代具備的真實生產函數完全不同,傳統金屬貨幣時代的貨幣是資產,且一旦形成增量,即為政府所有,因而形成購買力切割的鑄幣稅。在現代主權貨幣時代,貨幣發行很可能是對資產持有人的補貼,因而具有鮮明的轉移支付效應。
第六個共識是貨幣政策規則。如果如我們所論證,貨幣增量既是中性的,也是非中性的,在一定條件下還是超級中性的,那麼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間目標和貨幣供應量規則都需要修訂。從最終目標看,貨幣政策應該盯住扣除了金融業增加值的增加值。從中間目標看,貨幣政策應該盯住一籃子價格穩定性,包含 PPI(生產價格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和一切具有金融屬性的資產價格。從貨幣政策規則看,我們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弗裡德曼規則、泰勒規則的有效性和侷限性,或許還需要設定新的簡單易行的流動性管理規則——比如,廣義貨幣增長率= 扣除金融部門的增加值增長率 + 摩擦係數;基礎貨幣增長額 = 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增加額 - 居民儲蓄存款增加額。我們將通過模型模擬以重現1991 年、1997 年和 2008 年曆次重大危機前後的貨幣政策選擇。
第三個問題:隨著各國或激進或漸進地走進數字經濟時代,世界貨幣的穩定性及其演進方向如何?這一問題的處理難度遠遠超過前兩個。這是因為,對於前兩個問題,我和劉學博士的爭論只基於一個共識——事實是什麼,以及我們的解釋是否符合真實世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猜測甚至“押寶”的成分陡增,因而在分析方法上需要特別小心,任何演繹推理而非事實歸納很可能因遺漏重要的自變量而變得完全不符合未來的真實世界。在貨幣經濟學的預測與實踐領域,值得高度尊敬的有兩個人——剛剛去世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和至今不知為何方神聖的中本聰。前者一生堅持匯兌是冗餘的交易成本觀念,經歷了單一貨幣區理論在歐元區的實踐,但沒有也很難實現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烏托邦。後者眼睜睜看著自己一手締造的比特幣(bitcoin)演變為極其昂貴的數字資產,當前,全世界每年為挖掘最後200 萬個幣所耗費的能源足夠上億人使用一年以上。按照邊際成本定價法,比特幣越接近資產則距離廣泛流通的貨幣越遙遠。那麼,數字時代的世界貨幣(或世界貨幣體系)可能會長成什麼樣?我和我的學生們作了如下猜想。
在形成猜想之前,一定要強調一個基本前提——數字時代。數字化進程使得非數字時代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得以系統性降低,甚至歸零。在此前提下,諸多在簿記時代手工計算無法實現的瞬時交易成為可能。如此,才有我們的猜想。
第一個猜想是充當世界貨幣的主權貨幣“三元悖論”的非存在性。當然,隨之而來的是“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也將不復存在。這是因為,真實世界的世界貨幣肯定存在一個返程投資市場。換句話說,一切外匯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持有人所謂的外匯賬面資產,或者以該種貨幣資產形式存在,或者以離岸市場的貨幣資產形式存在。無論哪種形式,在一個充分套利的市場上,都會影響該貨幣的供應量或利率。因此,該貨幣發行國的中央銀行實際面臨的是全球貨幣需求,而非本國境內的貨幣需求。故,所謂貨幣政策自主權與資本自由流動的衝突並不存在。
第二個猜想是世界貨幣是主權貨幣當局的條約,或者說是超主權貨幣。Libra 構想的提出,核心是“穩定幣”。因此,我和學生們的實驗是基於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在締約國間基於人工智能(AI)算法設計一種基於浮動份額與套算匯率的數字穩定幣。無論在銀行間市場,還是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內,抑或家庭部門與企業部門相互間的零售交易,都可以實現主權貨幣與超主權穩定幣的雙幣結算和清算。這在技術意義上並非難題。早在 10 年以前,我赴海外出差時,用銀行卡購物就可以選擇按人民幣、美元或歐元計價。一籃子貨幣相對於單一貨幣的波動幅度更小,這對於跨境投資和貿易的優勢顯而易見。當然,這一穩定幣機制與歐元不同,其並不取消各國的主權貨幣,因而也不影響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不過,我們的算法將把任何一個參與國的貨幣發行自動折算權重(理論上可以在 0—100% 波動,0 意味著被自動剔除;100% 意味著參與國事實上實施了貨幣局制度),因此,貨幣籃子權重具有浮動性。這同時可能構成對各國貨幣發行的紀律性約束。從當前自由貿易協定現狀看,全球很可能出現一個或多個超主權貨幣,在超主權貨幣基礎上,還可以形成新的貨幣籃子組合。
第三個猜想是超主權貨幣對金融市場的改造。如果真的出現條約形式、來去自由、算法透明、匯率套算的超主權貨幣,那麼跨時區的金融市場就可以實現對同一標的按照同一穩定幣的無限連續交易。此時,一家上市公司或一個發債主體,在不同市場的融資具有完全等價性。屆時,將不會存在主權貨幣之間的世界貨幣之爭,也不會存在私人數字貨幣對主權貨幣地位的侵蝕。所謂外匯儲備,在貨幣意義上就是一個浮動權重的主權貨幣籃子。
猜想終歸是猜想。不過,人類貨幣史上的猜想轉化為現實的實例是有跡可循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即源於猜想。在我們猜想時,我始終以 Keynes(1936)的名言警醒我和我的學生——“有一些狂野的猜想似乎天馬行空,得自於天籟。但是,其思想內核無非是數百年前某個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家的想法而已”。當前,數字資產正在走金本位的老路,穩定幣構想也無非是“軟版本”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現實提法,我們的想法也並不見得比 1945 年的懷特計劃更高明。僅僅因為在數字時代,陳年老酒貼上了新標籤而已。
不得不承認,很多事情做著做著就變得不再是原先設想的樣子,很多工作幹著幹著人就變老了。我們寫作的初衷僅僅是對某個階段貨幣政策及其後續影響的討論,結果卻演變為三卷本的《貨幣論》。
對貨幣循環、貨幣政策和世界貨幣演進的理解加深了我們對真實世界貨幣經濟的認知。貨幣經濟從未達到過“完美”,一般均衡僅僅停留在我們的想象或期望中。每一次針對“不完美”的制度演進,通常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會引發新的問題,無論是本意在提高金融中介安全性的抵質押安排,還是本意在遏制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管理,或者本意在降低匯兌成本的世界貨幣制度,從時間序列的角度看,概莫能外。作為樂觀主義者,我和我的學生們完全無意否定任何既有的貨幣演進路徑,我們的努力旨在說明:任何貨幣理論和優化思考都存在瑕疵,我們的想法也不例外,在將來也可能會過時。
兩千年前,史學家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給出了思考者的最高境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和我的學生們的努力,遠無如此高遠的終極理想,而僅僅期望《貨幣論》能夠具備詮釋現實貨幣運行的能力,同時成為大學經濟學本科高年級學生和貨幣經濟學研究生觀測、理解、分析貨幣經濟的工具書。因此,三卷通篇不是依靠某種現成理論以解釋某個國家、某種貨幣工具所帶來的特殊貨幣現象,而是給出一切仍然存在“貨幣”這一經濟現象的經濟體必然面臨的外在表現及其內在邏輯。在這三卷中,讀者看不到關於國情、間接融資或直接融資主導、發展中國家或發達經濟體等特殊性,我們呈現的僅僅是一般理論。顯然,這一分析框架不一定符合貨幣演化史,不一定滿足所有的邏輯條件,不一定契合未來世界的貨幣循環,更不可能適用於極其特殊的情形,但它應該符合我從事貨幣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這三十年真實世界貨幣運行的一般狀態。
理論之不足促使人思考。借用 Kydland 和 Precott(1996)之問作為全卷寫作的動因:“檢驗理論的方法就是看看這個理論構建的模型經濟是否能夠模擬真實世界的某些方面。也許對一條理論而言,最大的考驗是它的預測是否能被現實所證明——也就是說,當選擇了某項政策時,真實的經濟是否會像模型經濟當中所預測的那樣?”
缺乏歷史觀的經濟學家是不具遠見的,缺乏現實解釋力的理論是不具生命力的。僅此而已。